【电影】杀人者报告丨인터뷰丨살인자.리포트【2025】

中文名: 杀人者报告
片名: 살인자 리포트
年代: 2025
导演: 曹英俊
编剧: 曹英俊
主演: 郑成日 / 曹汝贞
类型: 犯罪
制片国家/地区: 韩国
语言: 韩语
上映日期: 2025-09-05(韩国)
片长: 108分钟
又名: 인터뷰 / Muder Report
IMDb: tt37718411
豆瓣评分:
杀人者报告的剧情简介:
《杀人者报告》(살인자 리포트,2025):采访桌后的人性深渊与媒体困局
作为 2025 年韩国犯罪类型片的重磅之作,《杀人者报告》由曹英俊自编自导,郑成日、曹汝贞两位 “演技派戏骨” 领衔,以 “连环杀人犯专访” 为核心切口,将镜头对准 “真相与流量的博弈”“罪恶与救赎的边界”,在封闭的审讯室空间里,上演了一场比刀刃更锋利的心理对决。影片摒弃了传统犯罪片 “追凶缉拿” 的爽感叙事,转而深入人性褶皱与社会病灶,成为一部 “用对话剖开罪恶,用细节叩问良知” 的深度作品。
一、剧情脉络:从 “独家采访” 到 “致命陷阱” 的螺旋式反转
影片的核心场景集中在首尔看守所的审讯室 —— 渴望凭借独家报道翻身的记者善珠(曹汝贞 饰),顶着 “为 11 名受害者讨公道” 的名义,申请对连环杀人犯泳勋(郑成日 饰)进行 “一对一专访”。此时的泳勋已认罪伏法,却始终拒绝透露作案动机与关键细节(如第 11 名受害者的尸体去向),而善珠的出现,恰好成为他打破 “沉默” 的契机。剧情以 “三次采访” 为节点,层层揭开比杀人案更黑暗的真相:
1. 第一次采访:“猎人” 与 “猎物” 的身份错位
善珠最初带着明确的 “职业野心” 而来 —— 她准备了精心设计的问题(“第一次杀人时的感受”“为什么选择这些受害者”),试图用 “道德谴责” 逼迫泳勋吐露细节,为报道制造爆点。但泳勋的反应完全超出预期:他不辩解、不忏悔,反而冷静地观察善珠的微表情,甚至反问她 “你真的关心受害者吗?还是关心‘独家报道能让你升职’?”。这场对话中,“猎人” 与 “猎物” 的身份悄然反转:善珠的急切与功利被泳勋精准捕捉,而泳勋的 “配合” 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 “筛选”—— 他通过善珠的反应,判断她是否有勇气揭开 “案件背后的事”。影片在此埋下伏笔:泳勋墙上的律师会见记录显示,他曾多次拒绝警方提审,却唯独同意善珠的采访,暗示他的目标从不是 “认罪”,而是 “借记者之口传递信息”。
2. 第二次采访:“11 人命案” 的真相裂缝
随着采访深入,泳勋开始零星透露 “异常细节”:他描述第 3 名受害者时,提到对方 “手腕上有特殊的烫伤疤痕”;说起第 7 名受害者,反复强调 “她死前在给某个人打电话,说‘他们要来了’”。这些细节与警方公布的 “随机杀人” 结论矛盾,善珠敏锐地意识到: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连环杀人案,受害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,甚至泳勋只是 “执行者”。此时剧情引入 “第三方压力”:警方突然禁止善珠继续采访,理由是 “案件涉及敏感信息”;善珠的报社也收到匿名威胁,要求撤下相关报道。这些阻力反而坚定了善珠的追查 —— 她通过私下调查发现,11 名受害者中,有 6 人曾在 5 年前的 “三星重工污染案” 中作证,而泳勋的父亲正是当年污染案的受害者,因拒绝妥协被 “意外” 身亡。至此,“复仇” 的轮廓浮现,但泳勋的目的仍未完全揭开。
3. 第三次采访:“罪恶的传递链” 与自我牺牲
最终采访中,泳勋全盘托出真相:他并非 “主动杀人”,而是被某财阀势力胁迫 —— 对方以他女儿的性命为要挟,要求他 “清理” 当年污染案的证人,而第 11 名受害者(财阀内部人员)因掌握 “污染案与政商勾结” 的证据,被灭口后嫁祸给泳勋。泳勋选择配合善珠,是希望她能通过报道曝光财阀黑幕,同时保护女儿(他已将女儿安置在安全地方,自己则做好 “顶罪到底” 的准备)。影片的高潮并非 “黑幕曝光” 的爽感时刻,而是善珠的抉择:她手中握有泳勋提供的录音证据(财阀胁迫的对话),但发布报道意味着泳勋会被财阀灭口,不发布则 11 名受害者的 “冤屈” 永远无法昭雪。最终,善珠选择 “拆分报道”—— 先公布 “污染案与受害者关联”,引发公众关注,再通过匿名渠道将证据交给独立检察官,为泳勋争取 “翻案” 空间。而泳勋则在采访结束后,用藏在牙套里的刀片划伤颈动脉,以 “自杀” 拖延时间,为证据传递争取窗口期。
二、角色深度:不是 “善恶对立”,而是 “困在系统里的人”
曹英俊没有将角色塑造成 “非黑即白” 的符号,而是赋予善珠与泳勋 “双重困境”—— 他们都是被社会规则、职业身份、个人执念裹挟的 “普通人”,只是选择了不同的 “对抗方式”。
1. 善珠(曹汝贞 饰):媒体人的 “良知与野心” 拉锯战
曹汝贞跳出了 “正义记者” 的刻板印象,塑造了一个 “有瑕疵、有挣扎” 的立体角色:
她的 “动机不纯”:开篇的善珠,正处于职业低谷 —— 此前因报道 “校园霸凌” 时引用失实信息,被读者投诉、报社降职,她急需 “连环杀人案专访” 证明自己,甚至在第一次采访前,就和编辑预定了 “头版头条” 的版面;
她的 “良知觉醒”:促使她转变的不是 “道德感”,而是泳勋的一句话:“你写的报道,会让受害者家属觉得‘亲人的死只是你的晋升阶梯’”。此后,她开始主动走访受害者家庭,看到第 3 名受害者的母亲仍在寻找女儿的 “遗物”(一只手工手链)时,才真正理解 “真相” 不是 “流量密码”,而是 “给生者一个交代”;
她的 “现实妥协”:影片结尾,善珠没有成为 “英雄”—— 她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污染案的关注,但财阀势力并未被彻底扳倒,她自己也因 “违反新闻伦理”(未经警方允许发布案件细节)被报社停职。这种 “不完美的结局”,恰恰还原了媒体人的真实困境:在 “系统压力” 下,良知能做到的,或许只是 “不彻底妥协”。
2. 泳勋(郑成日 饰):“杀人犯” 外衣下的 “受害者与反抗者”
郑成日以 “克制到极致” 的演技,赋予泳勋 “令人恐惧又心疼” 的复杂气质 —— 他不是传统犯罪片里的 “恶魔”,而是 “被罪恶吞噬的普通人”:
他的 “恶” 是被迫的:影片通过闪回片段展现,泳勋曾是一名普通的机械师,女儿患有罕见病,他每天打两份工凑医药费。财阀势力正是抓住这一点,以 “给女儿治病”“保证女儿安全” 为诱饵,逼迫他走上杀人之路;
他的 “善” 是隐晦的:在描述杀害第 7 名受害者时,泳勋突然停顿,低声说 “我给她留了时间打电话,让她和家人说再见”—— 这个细节暴露了他的 “人性未泯”;而他最终选择 “自杀”,既是为了保护女儿,也是为了 “赎罪”(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手上的鲜血);
他的 “悲剧性”:泳勋的最大悲剧,在于他 “对抗系统的方式” 本身就是 “系统的一部分”—— 他想用 “认罪顶罪” 的方式揭露黑幕,却最终仍被系统(财阀、司法)操控,连 “死亡” 都成了 “拖延时间的工具”。
三、主题内核:犯罪片外衣下的 “社会批判三重奏”
《杀人者报告》的深度,在于它没有停留在 “个案正义” 的层面,而是借 “采访” 这一行为,剖开了韩国社会的三大病灶:
1. 媒体伦理的 “失序”:当 “真相” 成为 “流量的附庸”
影片对媒体行业的批判极为尖锐:善珠的报社编辑在得知她拿到采访机会时,第一反应是 “能不能让泳勋摆个‘忏悔的姿势’拍照”;某电视台为了抢热度,甚至伪造 “泳勋童年家暴” 的假新闻;而善珠最初的心态,也代表了部分媒体人的困境 —— 在 “点击率至上” 的行业规则下,“良知” 往往要让位于 “流量”。影片中最具讽刺性的一幕:当善珠发布 “污染案与受害者关联” 的报道后,公众的关注点很快从 “案件真相” 转移到 “善珠是否借报道炒作”,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她的谩骂(“为了红不择手段”“利用受害者博眼球”)。这种 “舆论反噬”,恰恰揭示了现代媒体的悖论:媒体本应是 “真相的传递者”,却在流量逻辑下,沦为 “公众情绪的消费品”。
2. 司法系统的 “失效”:当 “正义” 向 “权力妥协”
影片中的警方与检察官,不再是 “正义的化身”,而是 “权力的附庸”:警方明知泳勋的案件存在疑点,却因 “上级压力” 草草结案;独立检察官在收到善珠的证据后,也因 “担心影响与财阀的关系” 迟迟不立案。这些细节并非虚构,而是映射了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 “财阀干政”“司法腐败” 问题(如 “三星集团丑闻”“亲信干政案”)。泳勋在采访中说的一句话,道破了这种 “失效” 的本质:“他们(财阀)不怕我杀人,怕的是我说出‘谁让我杀人’—— 因为杀人是‘个体罪恶’,而幕后指使者是‘系统罪恶’,后者更可怕。”
3. 人性的 “灰度”:没有绝对的 “善” 与 “恶”
影片最核心的主题,是对 “人性二元论” 的颠覆:善珠不是 “完美的正义者”,她有野心、有妥协;泳勋不是 “纯粹的恶魔”,他有无奈、有救赎;甚至胁迫泳勋的财阀手下,也在最后时刻偷偷给善珠传递了 “泳勋女儿的藏身地址”—— 这些细节都在说明:人性不是 “非黑即白” 的画布,而是 “灰色的褶皱”,在不同的处境下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“善的执行者” 或 “恶的帮凶”。
四、视听风格:封闭空间里的 “心理张力美学”
曹英俊擅长用 “极简的镜头语言” 营造 “极致的心理压迫感”,影片 90% 的场景集中在审讯室,却通过细节设计,让 “封闭空间” 成为 “人性的放大镜”:
1. 色调与光影:冷色里的 “情绪裂缝”
影片全程采用 “低饱和冷色调”,审讯室的墙壁是灰蓝色,灯光是惨白的荧光,只有善珠带来的 “受害者照片” 是唯一的暖色(照片里的受害者笑容灿烂)。这种 “冷与暖” 的对比,既是 “罪恶与美好” 的隐喻,也暗示了 “人性中的微光”—— 即使在最黑暗的审讯室里,仍有 “追求真相” 的温暖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“光影的变化”:第一次采访时,灯光直射善珠的脸,暴露她的急切与紧张;第二次采访时,灯光逐渐向泳勋倾斜,他的面部一半在阴影里,一半在光亮中,象征 “罪恶与良知的并存”;第三次采访时,灯光突然闪烁(暗示财阀势力在监控),最终彻底熄灭,只剩下善珠手机的手电筒微光,照亮泳勋递过来的录音笔 —— 这束 “微光”,成为 “真相与希望” 的具象化表达。
2. 镜头与剪辑:特写里的 “心理博弈”
影片大量使用 “面部特写镜头”:善珠的手指反复摩挲采访本的边缘(暴露她的焦虑),泳勋的瞳孔在提到女儿时微微放大(暴露他的软肋),这些微表情细节,比台词更能传递角色的心理变化。剪辑节奏则随着 “采访进程” 逐渐加快:第一次采访用 “长镜头”,展现对话的 “拉锯感”;第二次采访加入 “闪回片段”(受害者生前画面、泳勋的家庭回忆),碎片化地补充真相;第三次采访则用 “交叉剪辑”,一边是审讯室里的对话,一边是善珠的同事在报社传递证据,一边是财阀手下在看守所外待命,三线并行,将紧张感推向高潮。
结语:不是 “谁是凶手”,而是 “为什么会有凶手”
《杀人者报告》最终没有给出 “完美的正义结局”—— 财阀势力虽受重创,但未被彻底清除;善珠失去了工作,却坚守了良知;泳勋的女儿得到了保护,但永远失去了父亲。这种 “不完美”,恰恰是影片的价值所在:它没有迎合观众对 “爽感” 的期待,而是迫使我们思考:比 “抓住凶手” 更重要的,是 “为什么会有凶手”?比 “曝光黑幕” 更难的,是 “如何改变产生黑幕的系统”?当影片结尾,善珠站在受害者纪念碑前,将泳勋留下的录音笔埋在第 11 名受害者的名字下时,镜头缓缓拉远,纪念碑上的名字逐渐模糊 —— 这或许是导演的隐喻:个体的罪恶会被遗忘,但系统的病灶若不根治,新的 “受害者” 仍会出现。而像善珠、泳勋这样 “不彻底妥协” 的人,正是对抗这种 “遗忘” 的微光。
请在这里放置你的在线分享代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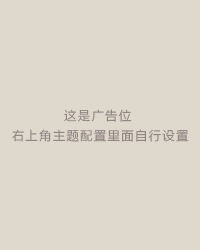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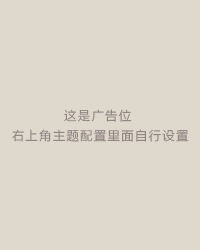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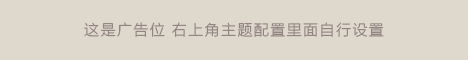
本文暂时没有评论,来添加一个吧(●'◡'●)